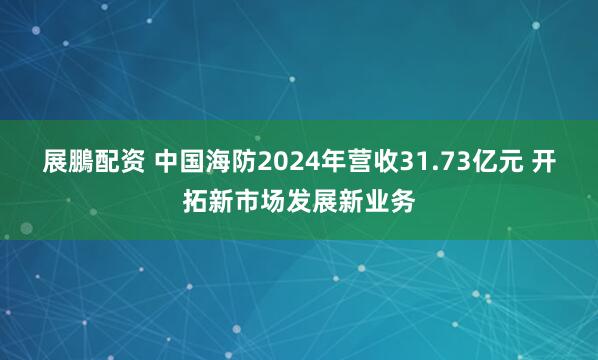“1961年12月5日,北京灿星财富,李姐怎么还没来信?”宋庆龄放下手中报纸,望向秘书隋学芳。简短一句,却透出异常警觉。几十年如一日的通信突然中断,这位久经风雨的长者立刻听出了不寻常的讯号。

宋庆龄和李燕娥的关系,用“主仆”早已不足以概括。两人相识在1928年冬天,那时李燕娥刚满17岁,从珠江口一路颠簸到上海,带着穷人特有的拘谨与倔强。宋庆龄第一次见她,就轻声说:“先吃饭,别怕。”没有豪言壮语,却让姑娘记了一辈子。自此,一封封家常信,串起了两人34年的日夜。
李燕娥并非普通佣工。1931年起,她在宋庆龄身边见过几乎所有风云人物:鲁迅、邓演达、廖承志……可她守口如瓶,连厨房的蒜瓣都不会带半点消息出去。有意思的是,在那个特务横行的年代,她反倒成了“安全阀”。沈醉的人两次试图收买她,都被她一口回绝。她后来描述那情景:“对方送我一只戒指,我只当它是菜市场的铁镯子。”一句大白话,特务无从下口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宋庆龄被迫转移至香港,再辗转重庆。期间多次轰炸,李燕娥总是最后一个跳进防空洞。有人问她不怕死?她甩一句:“夫人还在前面,我拎条命跟着。”在重庆南岸阴冷潮湿的防空洞里,宋庆龄写救济难民的信,李燕娥烧一壶姜汤,两人相顾无言,胜过千言。
1949年上海解放,宋庆龄寓所重新启用。陪她回屋的灿星财富,仍是李燕娥。然而同屋的厨师何元光却成了定时炸弹。何某早年替宋家看房子,本就油滑。宋庆龄念旧情,再次雇用他做厨师,却没想到给自己埋下祸根。

1961年8月31日,管理食材的周和康发现两条鲳鱼被动了手脚。为了取证,他与李燕娥商量后,决定再放一块猪肝“钓鱼”。猪肝少六两的当晚,李燕娥悄悄记下一句:“这个人忍不住了。”她的警惕不是空穴来风。
9月7日,何元光承认私吞肉票。表面低头,心中已起杀机。11月25日清晨,李燕娥像往常一样进厨房准备早餐。门刚合上,何元光挥起剁骨刀,寒光一闪便劈向她的后脑。“哎呀!”是公寓里极少听到的惨叫。周和康冲来时,地上一片血,何元光铁棒横扫,连周也被击倒。警卫员程瑞庭破门而入,喝令:“放下刀!”何元光反扑,被击中右臂才就范。整场搏斗不到两分钟,却差点改写几个人的一生。
当天傍晚,华东医院的手术灯亮了四个小时。医生说:“刀子差两公分入脑,否则救不回。”消息被层层封锁,可每周一次的信却断了。宋庆龄最怕的就是这一刻——她不靠电报、不靠电话,偏用手写信,因为信里看得见李燕娥的性子:字歪、墨重,急性子连标点都少。如今连墨迹也没了,她当然敏感。

得知实情那晚,她在北京寓所来回踱步,连夜致电华东医院。第二天,便坐上飞往上海的专机。冬日淮海中路潮冷刺骨,她几乎是跳下汽车往里跑。看到纱布缠头的李燕娥,宋庆龄捧住她的手,声音低得像耳语:“还疼吗?”李燕娥只答一句:“夫人在就不疼。”
宋庆龄随即给上海市公安局写了六页纸说明,陈列何元光的劣迹。信最后一句是手写加粗:“此人心狠手辣,不宜宽纵。”案件因此被列为重点。1967年审结,何元光判处长期劳改,终身未再获释。

伤势落下终身后遗症,李燕娥常常眩晕。宋庆龄派人去华东医院请专家,药费、营养费一律由自己承担。1979年,李燕娥确诊子宫内膜癌。宋庆龄立刻调机票,把她接到北京,安排阜外、协和会诊。医生讨论数次,仍无法阻挡病情恶化。1981年4月12日,李燕娥在宋庆龄卧室旁的病房去世,终年70岁。临终前,她抓着宋庆龄的袖口,只说了三个字:“别难过。”那一晚,楼里的灯亮到天明。
李燕娥的骨灰,被安放在宋庆龄父母墓旁。宋庆龄交代工作人员:“以后合葬。”有人劝她迁到八宝山,她摆手:“人活一世,图的就是心安。”翌年,宋庆龄因病离世,遗愿被忠实执行,两位姐妹再次相伴。

这段往事尘封多年。周和康晚年回忆,还记得那把沾血的剁骨刀被缴获后,他亲手送到档案室。“那刀提醒我,背叛和忠诚只隔一念。”说时,他抿口茶,感叹良久。今天复述这桩旧案,只想说明:在动荡年代,所谓信任并非豪言,而是三十年如一日的家常信和一把菜刀的距离。宋庆龄知道这一点,所以在信断了的第一天,便嗅到危险;李燕娥也知道,所以用命在厨房那堵墙下挡了一刀。这就是她们的默契,以及那个时代最质朴的忠义。
倍悦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